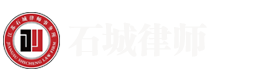-
石城研究
某槺公司于2011年1月11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有三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翁某棠,持股比例为90%;钱某恩,持股比例为5%;张某静,持股比例为5%。2011年张某静被聘为公司监事,任期三年,之后未重新选任监事。 2017年7月10日,宁波某基层法院作出(2017)浙0203民初10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某槺公司支付称某仕公司货款490余万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2017年10月30日,某仕公司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2017)浙0203执3026号执行裁定书,以某槺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某仕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何某,2023年4月23日公司自行注销。2024年2月29日,该院作出(2023)浙0203强清6号民事裁定书,以某槺公司未提交账册、重要文件等材料,致使清算程序无法进行,且目前无可供清算的财产为由,终结某槺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何某遂起诉张某静、翁某棠、钱某恩就某槺公司欠何某490余万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翁某棠、张某静就某槺公司欠付何某的490余万元及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钱某恩不承担责任。 张某静不服一审判决,遂上诉(案号(2025)浙02民终1337号),称:监事均不是公司清算义务人,因此不论张某静是否担任监事,均不应以此为由在张某静与钱某恩之间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且张某静在某槺公司清算的法定情形发生时,不是某槺公司的监事。不存在张某静怠于履行义务的情形:张某静在2014年1月以后因怀孕生子从某槺公司离职,案涉债务、翁某棠卷走案涉货款的事实均发生在张某静离职之后。张某静在公司的占股比例仅5%,与另一股东钱某恩5%的股权相加也仅有10%,不足以形成任何公司决议,也不是公司执行机构或决策机构成员,无法成立清算小组进行清算,因此并非怠于履行义务。某槺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不是股东怠于履行义务所致。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只有在股东怠于履行义务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股东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不存在张某静怠于履行义务的情形,因此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二款中的“怠于履行义务”可以举证推翻,若股东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或者小股东举证证明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则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股东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主张其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张某静被选举为某槺公司监事并经工商登记,张某静虽主张其于2014年1月监事任期届满,并从某槺公司离职,对公司经营情况并不知情,但根据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登记信息,张某静仍为某槺公司的监事。《公司法》第77条规定,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履行监事职务。张某静作为公司监事,应当履行职务,但其未申请某槺公司强制清算、亦未举证证明其为履行清算义务作出了实质性努力,应当认定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现某槺公司账册丢失,虽然张某静举证称账册丢失并非其过错,但张某静作为公司监事,应当履行检查公司财务的义务,故某槺公司账册丢失与张某静的消极不作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张某静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同时就,两小股东之间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法院认为,张某静与钱某恩虽然均为某槺公司股东,但身份不同,张某静不仅是公司股东,且担任公司监事职务,有义务对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监督,而钱某恩既未担任公司职务,也无证据证明其参与公司经营,符合“小股东举证证明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免责条件,故一审法院判决钱某恩不对某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清算事实发生在公司法施行前,因清算责任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适用2018年版公司法规定。 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二款规定,认为张某静虽未小股东,但是作为监事,参与了某槺公司经营,且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清算,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法院则认为张某静作为监事,未履行检查公司财务的义务,未申请某槺公司强制清算、亦未举证证明其为履行清算义务作出了实质性努力,应当认定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判决维持原判。 笔者认为,按照《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二款和《九民纪要》第14条、第15条规定,判决两个小股东不同责任,即担任监事的张某静承担连带责任、未任职的钱某恩不承担责任,尚算有法可依。但是二审法院认为,张某静作为监事,因“未申请某槺公司强制清算、亦未举证证明其为履行清算义务作出了实质性努力”,应当认定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超过了法律规定,有商榷余地。 我国公司清算,包括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解散清算依据清算人的选人不同,分成自行清算和强制清算。1 强制清算不是普通清算,而是指定清算。2 公司解散是由出现后,应当清算,然后结束公司法人人格。清算时,有两种人出现:清算义务人和清算组织,两种人的义务是不相同。 2018年公司法没有规定清算义务人,仅规定有限公司清算组由股东组成。法院一般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二款,认为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为股东。但是《民法总则》以后,备受争议,因为《民法总则》规定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前述案件一审法院即按照《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二款规定,认定张某静为清算义务人。 清算组由清算义务人依法成立,2018年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 但是,实践中,法院适用《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二款出现大量问题,比如职业债权人向小股东主张权利。因此,《九民纪要》就该条中“怠于履行义务”加以说明,认为小股东不是董事、监事,未派员担任董事、监事,为参与经营的,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上述案件中,一审法院亦即以此观点,判决另一小股东不承担责任;而张某静需要继续履行监事职责,因此不能适用该免责情形。 对新公司法以后的监事,具有警示作用的是,该案中二审法院的关于“怠于履行义务”意见。 如上述,清算程序中有清算义务人和清算组两种人(组织)。其中,清算义务人的义务是积极行为义务,需要及时启动清算程序,成立清算组。该行为义务不能简单易结果论,如小股东要求控股股东成立清算组,未达到回应,清算组未成立,从而认定怠于履行义务。 问题关键之一是,谁是清算义务人,新公司法之前,实践中一般认为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为股东,新公司法以后为董事。没有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公司监事为清算义务人,监事仅为监督机构(成员),不具有启动清算程序,成立清算组的义务。 申请强制清算的主体,2018年公司法第183条规定仅为债权人,《公司法解释二》(2020年修正)第7条扩张为债权人、股东、董事或其他厉害关系人。没有明确规定申请主体包括监事(会),监事申请,只能将之解释为其他厉害关系人申请。同时,未向法院申请指定清算组,不算“怠于履行义务”。3 新旧公司法均为规定,监事应为清算组成员,因此不应当承担清算事务执行中,违反法律法规,造成债权人损害的赔偿责任。清算组成员怠于履行义务,犹如公司董事执行公司事务,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清算程序工作。上述案件中,张某静非清算组成员,不应承担责任。 因此,上述案件二审法院,认为张某静“未申请某槺公司强制清算、亦未举证证明其为履行清算义务作出了实质性努力,应当认定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实无法律依据。 而就监事的财务检查义务,不能推定具有保存财务账册的义务;且判决实际并未参与经营管理,仅挂名监事的小股东承担巨额的债务,有失公允。 该案适用2018年公司法,有限公司清算义务人为股东,新公司规定公司清算义务人为董事,均没有规定监事在清算程序中的义务。按照上述案件的逻辑,监事具有检查公司财务的义务,应当发现公司账册存管情况;具有申请强制清算的义务,应当督促清算义务人履行清算义务;否则将承担清算责任。 笔者认为上述案件不应当成为典型的案件,也不应当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对新公司法后监事亦有警示作用:需要积极履职,敦促董事、高管积极履职。辞任监事,需要敦促公司做工商变更,若公司未予以变更,应通过诉讼予以涤除登记,以免担责。
参考来源: 【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一)、(二)理解与适用》第2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9,第245页。 【2】施天涛著:《公司法论》地五版,法律出版社,2025,第532页。个人认为在主流教科书中,施天涛教授的该书,在此节描述更准确和精彩。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12,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