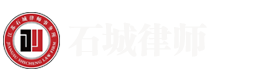一、案情简介
2014年3月27日,南京液压机械制造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液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向孙某出具借条,约定刘某向孙某借款100万元整。同日,孙某向刘某的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2014年10月17日,液压公司向孙某出具担保书,承诺对刘某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刘某未能如约偿还借款本息,液压公司未履行担保义务,孙某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履行还款义务,液压公司承担担保责任。2015年1月20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液压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为其指定了破产管理人。
庭审过程中,液压公司抗辩称,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公司为股东担保应当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但其为股东刘某借款提供担保并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故本案所涉担保行为无效。
法院审理后认定,首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并非是效力性的强制规范,违反该条款规定并不导致对外担保无效;其次,《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液压公司管理人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未提起撤销之诉诉讼,故液压公司应对刘某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二、公司对外瑕疵担保的法律效力
公司对外瑕疵担保,是指公司违反了《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超出了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保数额或者未经公司内部决议即对外向他人借款提供担保。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按照被担保人身份的不同,应遵循不同的表决程序。公司为非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可在这两种决议形式中自由选择,并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对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数额限制,《公司法》还赋予了公司可在公司章程中自主规定的权利。上文的案例中,液压公司的被担保人刘某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公司的日常生产和经营均由刘某负责,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液压公司为刘某提供担保,应当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而本案中液压公司提供的担保在形式上明显存在瑕疵,此时该担保的效力应如何认定?笔者认为,该担保是否有效,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性质分析
《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同时《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又进一步明确,“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相对的概念叫做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如果合同违反的是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则合同并不当然无效。
关于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的区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地,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简单来说,判断某项法律规定是否是效力性强制规范的标准,首先可以看该条规定中是否直接认定某行为或某合同无效,若未直接写明,则看该条规定中是否包含“禁止”、“未经……不能……”等否定性的词语或句式。若某项法律规定仅仅对某个行为的成立应具备的条件做了准入性的规定,而没有作禁止性或否定性的规定,则该规定一般可认为是管理性强制规范。而有关《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性质问题,笔者认为,本条规定应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首先,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这一行为本身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且《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并未直接规定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无效;其次,从目的解释的角度看,本条规定的立法宗旨在于对公司从事民商事活动进行规范和限制,即为了防止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利用公司的独立性和有限责任性谋取私利,从而侵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债权人甚至公司本身的合法权益;第三,由于法律具有公示力,该规定也意在督促担保权人应对公司提供的担保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在(2012)民提字第156号“申请再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被申请人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大连振邦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再审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该裁判思路也体现了最高法对本条规定性质属于管理性强制规范这一基本态度。
(二)担保权人善意与否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公司对外担保大多数是由法定代表人而为的,在本文开头的案例中,液压公司提供担保的债务人刘某也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前要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质上是一个公司股东以决议的形式,赋予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这一权限的过程,故公司未经内部决议对外提供担保,也可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行为。对该行为效力的认定,《合同法》第50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担保法解释》第11条也明确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故认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存在瑕疵是否有效,关键在于担保合同中的相对人即担保权人是否为善意。
相对人为善意,简言之即为不知情。笔者在上文分析《公司法》第16条性质时曾提到,由于法律条文具有公示效力,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经过公司内部表决通过这一程序性要件应该为全体公众所周知,故担保权人在与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时,应该对该担保的表决程序做必要的形式审查,如要求公司提供公司章程、与本次担保有关的决议、股东名录等材料用于查阅,并做好简要的复制、摘抄和记录工作,以证明自己尽到了注意义务。
民事法律关系中,证明“无”往往比证明“有”要困难得多,故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的标准不宜过于严格。担保权人对上述事项仅需作形式上的审查,即只要确认公司具备上述资料,且内容上可以互相印证即可,对于上述资料中的签名、形成时间、表决结果等具体信息是否真实,则不在担保权人的审查义务范围之内。同时,如果担保权人未能提供上述材料,也不宜就此认定担保权人非善意,还应结合本次担保的主债务的实际用途、提供担保前后的关联事实综合进行判断。就本文开头的案例而言,首先,主债务人刘某向债权人孙某所举的债务,主要用途为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液压公司的资金周转和生产经营;其次,债权人以转账形式将资金打入的银行账户非刘某的个人账户,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刘某已将该资金用于维持公司经营,而非挪为己用。故本案中,应将孙某视为善意相对人,并据此认定该担保行为有效。
(三)公司行使撤销权与否对瑕疵担保效力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案例中存在一个问题,即液压公司为刘某提供担保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7日,而液压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被法院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程序。《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上文的案例中,法院以液压公司的管理人未行使撤销权为由,认定液压公司的担保行为有效。笔者认为该论证过程的逻辑性值得商榷。首先,就《企业破产法》的该条规定本身而言,其限制的是公司对外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但公司对外提供保证担保这一行为的效力,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其次,撤销权系形成权,需要权利人主动提出,根据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诉讼当事人未提出的诉讼请求或主张,法院不宜主动审查。故本案中,法院应将论证的重点放在该担保行为本身,而不能以当事人是否提起撤销之诉作为担保合同有效与否的标准。
由于破产程序具有特殊性,法律更倾向于保护破产债权人的权利,防止公司恶意转移财产,故法律对破产程序中的撤销权的行使未作过多限制性的规定。但在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撤销权的法律后果并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民法总则》第85条规定,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由此可见,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是否行使撤销权,对于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并无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不能直接认定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无效,还应同时审查担保权人在担保合同的订立过程中是否为善意,并不以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为绝对性效力阻却事由。此种效力认定标准已在近几年许多司法判决中得以体现,这对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保护交易结果起到了良好的平衡作用。
张璋: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南京师范大学民商法学硕士。
方向:致力于民商法的理论与实务研究,主要业务领域包括婚姻家庭纠纷、企业法律服务及民商事合同纠纷。